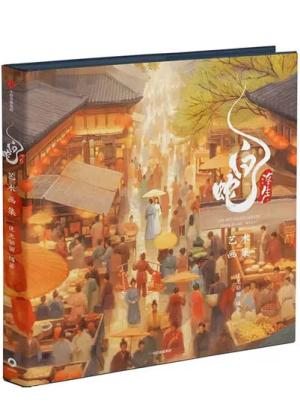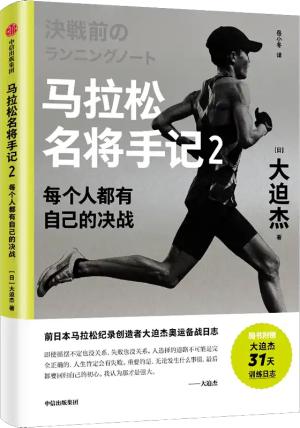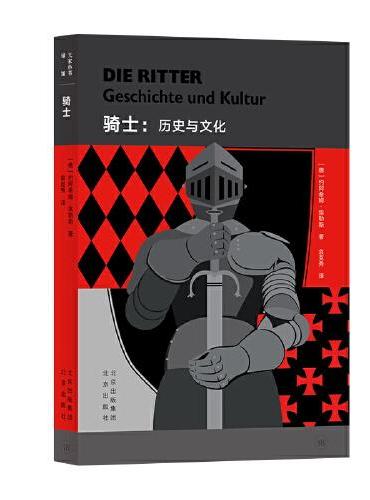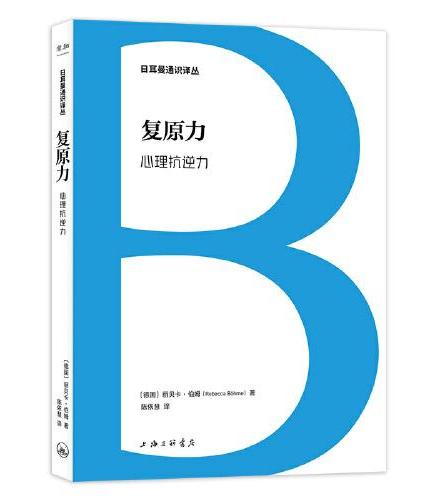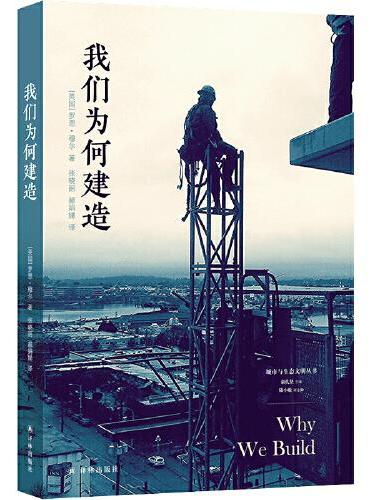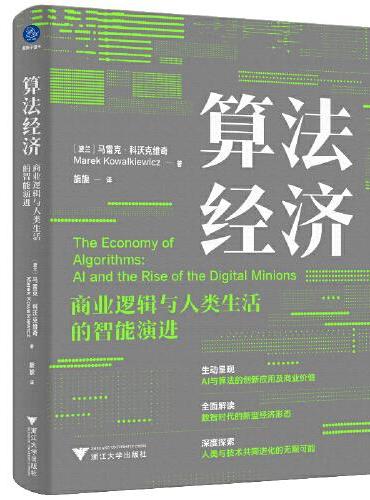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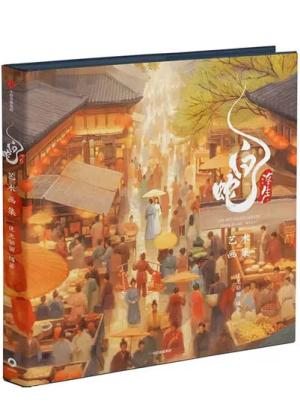
《
白蛇:浮生艺术画集
》
售價:HK$
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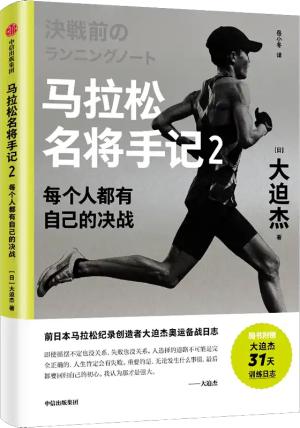
《
马拉松名将手记2: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战
》
售價:HK$
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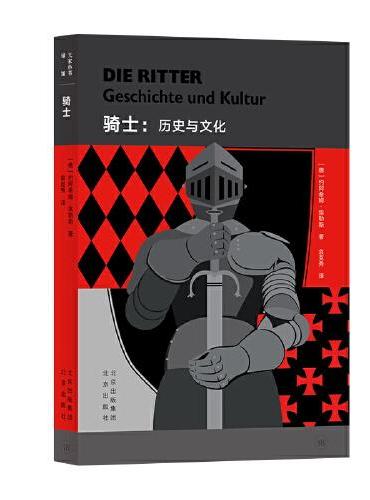
《
大家小书 译馆 骑士:历史与文化
》
售價:HK$
56.4

《
没有一种人生是完美的:百岁老人季羡林的人生智慧(读完季羡林,我再也不内耗了)
》
售價:HK$
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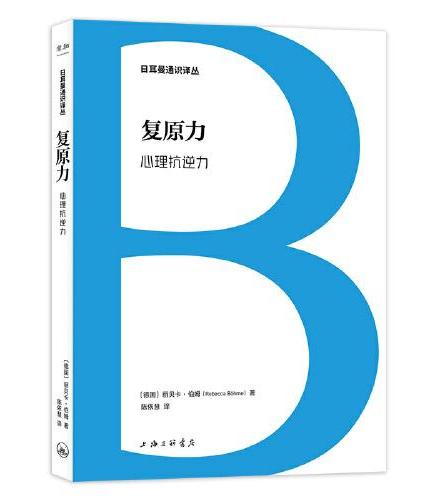
《
日耳曼通识译丛:复原力:心理抗逆力
》
售價:HK$
34.3

《
海外中国研究·未竟之业: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
》
售價:HK$
1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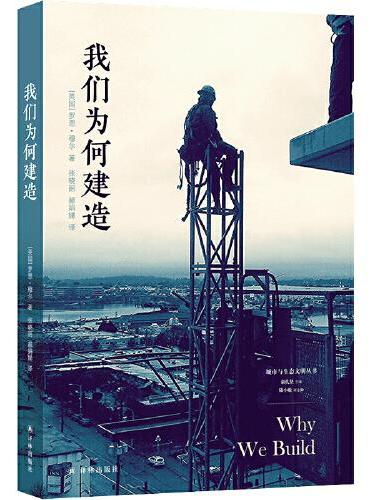
《
我们为何建造(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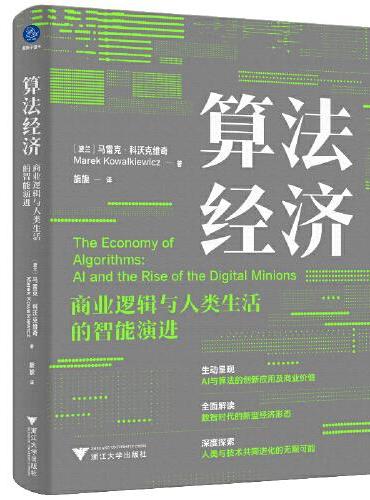
《
算法经济 : 商业逻辑与人类生活的智能演进(生动呈现AI与算法的创新应用与商业价值)
》
售價:HK$
79.4
|
| 編輯推薦: |
◎ 本书卖点
1.
这是日本传奇浪人宫崎滔天前半生的自传,一本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名著。论清末的革命宣传,章士钊所著《孙逸仙》一书的流传及其收效之宏,足以与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比驾。而《孙逸仙》正脱胎于宫崎滔天的原著《三十三年之梦》,成为清末“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为孙中山建立起一个有理想的民族革命家的形象,团结青年知识分子趋向他所领导的革命,改变了革命和保皇角逐的形势,可以说本书是中国革命运动进展中的一份传播革命思想的文献,发挥了很重要的历史作用。本书的中文节译本是清末最畅销的革命宣传书册之一,曾风行于中国内外,影响和教育了这一代的革命知识分子。举例而言,黄兴就是因读此书而得知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奠下了日后与孙中山合作共图革命大业的心理基础。宫崎滔天本人因自身的忠诚无私,在中国革命家和政治领袖中博得普遍的信任和敬重。1917年当滔天到湖南长沙参加黄兴的丧礼时,当时还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毛泽东曾致函滔天,对他称许说:“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
2.
本书是有关
|
| 內容簡介: |
|
《三十三年之梦》是宫崎滔天于惠州起义失败后,在一种经济极度拮据、心境极度愤怨的情况下写成的前半生经历的回忆录。全书分为二十八节。前半部叙述了滔天自己的家世,早年受教育的经过,他的大陆思想的产生与形成,以及早年在南洋、泰国等地的移民活动。后半部详细记录了他与中国革命活动的关系和经历,主要包括他如何结识孙中山和投身中国的革命运动,到华南去营救康、梁,运武器支持菲律宾的革命志士,促成华南、华中等地会党与孙中山的合作,以及参与策划惠州起义等事件,而以惠州起义失败后,他投身于浪花节界为生一事终结全书。对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日本明治时代社会问题,本书都富有价值。本书现收入“辛亥记忆”丛书。
|
| 目錄:
|
新修订版序林启彦
三联版原序一王德昭
三联版原序二林启彦
孙中山序
宫崎滔天自序
半生梦觉思落花
故乡的山河
我的家庭
中学和大江义塾
自暴自弃者的回头
成为耶稣教徒
思想的变迁和初恋
建立了根本方针
进入梦想中的乡国
无为的四年
远征暹罗
归国中的三个月
第二次远征暹罗
呜呼!二哥死矣
揭开新生的一面
再入梦想中的乡国
兴中会领袖孙逸仙
外行外交家
康有为到日本
南洋的风云和我党的活动
形势急转
大举南征
新加坡入狱
在“佐渡号”船中
运筹擘划悉皆失败
与孙逸仙书
惠州事件
唱吧!落花之歌
附录一:先父滔天的一些事迹宫崎龙介著林启彦译
附录二:宫崎寅藏(滔天)与中国革命活动编年纪要
林启彦编
人名索引
|
| 內容試閱:
|
序
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的中译本原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迄今已经历了三十载的岁月。此书自面世以来,一直深受中国读者欢迎,在史学界中,亦经常被征引援据。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重新排印本书,并列入近代中国贵重回忆录丛书中之一种,以垂久远,实为此书之幸。笔者乘此机会,得对本书重温一遍,并得仔细校订前版未及改正的错误,亦一美事也。在新版将要付梓之际,谨撰数言,以抒感怀。
宫崎滔天(1871—1922)是近代中日两国民间友好交往历史中最值得怀念和尊敬的人物之一,他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近代中国革命家建立的友谊及对他们的革命事业毕生的支持,可谓最诚挚感人。宫崎滔天一生有极不平凡的经历,他的思想是超前于时代的,他不像明治以来多数的日本人,理想的追求只停留在欧化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上,他提出支那革命主义(宫崎使用支那一词,绝无贬义——笔者),要支援中国以至亚洲各国受压迫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统治,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与和平的亚洲。这思想成为他终生奉献于中国革命活动的原动力。
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宫崎滔天选择了参与中国的辛亥革命运动为其行动的第一步。对中国革命领袖的支援,滔天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努力斡旋与奔走,许多被清廷通缉的政治犯,包括孙中山、黄兴等人,获得了庇护;他又促成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会面与合作,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重大作用。他主张中日提携论、土地国有、平均分享的思想,影响和启发了孙中山与黄兴等人的社会政治观。为了增强革命派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的活动能力,他在日本政界、留学生以及立宪派之间奔走撮合,争取他们支持革命,结成盟友,而自己则甘于做中介者的角色。他为了让日本社会知道中国人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首先翻译孙中山自撰的《伦敦蒙难记》为日文(1898年出版),撰写数量可观的纪实文学作品如《三十三年之梦》、《支那革命物语》、《清国革命军谈》等,尤以《三十三年之梦》影响最为深远。他还创办了《革命评论》(1906年),撰写大量的政论,以声援《民报》而大造舆论工作,为宣传革命思想及提高中国革命党人在国内外的道德形象,努力不懈。
这些工作,极大地鼓舞着不少海外和国内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日本人加入革命派的行列。他在经济与军事方面给予革命派实质的援助,缓和了当时革命党人极为拮据的财政状况,帮助解决革命军火筹措的难题,所以滔天对辛亥革命可谓贡献良多。为此,宫崎滔天得到了许多史家学者高度的赞誉与评价。卫藤瀋吉形容他是一位“唐吉诃德型的行动派”,近藤秀树称他是“日本的拉弗耶特”,詹逊(Marius B.Jansen)认为他是“众多日本志士中最重要的一人”,吉野作造评价他是建构“中国与日本间桥梁志士之一”等等。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国运岌岌可危,经历甲午战败和义和团事件以后,列强加紧分割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人亡国灭种的日子,迫在眉睫。处于如此危急存亡之际,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两股革新力量,试图通过两种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以促进中国的更新,救亡图存。其中之一是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温和的政治改革,欲仿效明治维新,推行君主立宪,但结果因保守派的反对及破坏而以失败告终。主张立宪改革的康、梁,被迫亡命海外,才能保住生命,致力迎救康、梁出险的,是宫崎滔天。另一场是由1895年起至1911年止,由孙中山领导的由下而上激烈的政治革命,以确立法美模式的共和民主制为理想,期间的革命起义失败了多次,到了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才最终成功,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民国。在这十多年策划起义的生涯和亡命海外的日子中,当孙中山事业最低沉、境况最恶劣的时候,给予孙中山有力的物质资助和精神支持者,是宫崎滔天。日本自明治维新以还,拥抱西洋文明,厉行欧化政策,脱亚入欧,国势迅速强大,摇身一变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员,与西方列强竞逐亚洲的霸权,日本朝野正为日本这些“文明”成就而欢呼喝彩之时,对日本“文明”发出质疑,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行径加以谴责,批判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呼吁日本应回归亚洲,做亚洲民族的忠实盟友,与他们一道联合起来,抗击西方列强,争取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政治在亚洲诸国实现的,是宫崎滔天。对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以来一贯的军国主义扩张侵略,予以痛责;对其对华政策一贯玩弄压制与利用的两面手法,深表不满;对大隈内阁的助袁和提出廿一条要求,以及寺内内阁的援段压南(南方革命军政府)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的,也是宫崎滔天。对日本军部的骄横跋扈,提出指责;对日本右翼民间团体如黑龙会、玄洋社等,以利用援助革命派的手段来谋求扩大日本在华的利权的做法,予以坚决抵制的,也还是宫崎滔天。是什么思想力量,主导滔天有这样坚强的侠义性格与独立特行的言行呢?
滔天是一位自始至终真诚拥护自由平等及民主共和理念的人。他更有一个民胞物与、人人平等的人道正义的信念。这样使他能发展出一种世界公民、世界革命的意识,以献身于全人类的自由与平等的事业。我们不妨引用他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自序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他是这样表白自己的:
我深信人类有同胞之义,故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我信奉四海一家之说,故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深恶之事,不可不除;憎厌之事,不能不去,否则世界大同的理想,就只是梦想。……所以我便以世界革命者自任。
滔天希望建设的是一个“车夫马夫有车坐,穷苦农民亦富有,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落花之歌》)的世界。
宫崎滔天以他的崇高的理想、侠义的胸怀、正直的言论,与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革命志士建立起真挚的友谊,共同促进双方国家的进步,谋求世界大同,树立起中日两国民间友好的典范。对两国人民来说,这段历史尤应珍惜重视。透过本书的记述,我们当可细味其中史实的一二。
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道路可谓无比曲折坎坷,两国人民始终无法建立坚强的互信和真正的友谊。我们期待廿一世纪的中日新关系,将能有所突破。廿一世纪,中日两国将更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发展友好邦交。廿一世纪的亚洲各国也将有更大可能建立和平、亲善与合作的新关系。今日中日两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若能以昔日宫崎滔天与孙中山等革命家的抱负和友谊为明灯、为资鉴,极力消除彼此之间的猜疑障碍,努力推动友好合作,则孙中山与宫崎滔天当年期待建立的民主、自由、和平、均富的亚洲盟邦,应不会是很遥远的事吧!
林启彦
二○一○年六月于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退休前夕
我性喜声歌,不论东西,不问文野,无论是《义太夫》或《法界》,也不管是《阿保陀罗》或《新内》,一切歌曲之类,即使人们认为是野鄙淫亵的东西,也无一不使我心旷神怡,只是自己尚未擅长此道而已。
我幼时曾记得《祭文》的一节:“只闻头领一声令,扶危解困献赤诚;江户美男人钦慕,长兵卫者是我名。”虽然仅此一段,但每当心情郁闷时,便高歌此曲以自慰。十数年来,东奔西走,受到了人世激浪不断的打击,对于此道,亦自觉略有进步。这是因为在心境不能平静的时候,便靠纵酒高歌以泄积愤。
数年前从华南归来,走访云翁〔头山满〕。他为我设下酒筵,供我痛饮,我于是乘醉放歌,他笑道:“如果你当年当了祭文说唱的演员,恐怕现在早已天下无双了。”后来我陪同康有为从香港归来,与中国志士陈白同访云翁,云翁送给我一个琵琶,陈君代他题了一首诗:
流落浔阳妇
冰弦诉别情
吴门乞食客
亦作洞簘声
英雄漂泊红颜老
同抱余情委秋草
赠尔琵琶作伴游
一拨十年长潦倒
呜呼!谁知此诗竟然成了谶语。当时我岂能想到会当浪花节的演员呢!
有人说:为人立志必须远大。又有人说:人没有自知之明,必会贻误一生。前者可以使人气壮,后者却使人志短。误于前者将陷于浮夸,结果一事无成;误于后者,则将萎靡不振,有负天赋。我是误于前者的吧!
我常想,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限制人的能力。如果轻率地断定终身而安于小节,那就简直是暴殄天赋。因此,我认为立志必须远大,要建立空前的伟业,以安天下苍生。
又有人说:理想是理想,未必能实行。我以为理想必能实行,不能行的是梦想。我深信人类有同胞之义,故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我信奉四海一家之说,故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深恶之事,不可不除,憎厌之事,不能不去。否则,世界大同的理想终是梦想。于是,我认为不靠实力是不行的,所以便以世界革命者自任。
我虽然一向认为人的力量,无穷无尽,但人生最要紧的事,在于个人的自觉。佛家所谓见性成佛,耶稣所谓以如上帝的完全,求自己的完全。要达到这个境界我认为只有靠学问与教化。学问与教化,一定要教育普及才可行。但社会不平等,贫者多而富者少,没有时间与金钱,教育无从说起。而希望教育能普及,又非首先改善大多数穷苦民众的生活不可。于是我又以社会革命者自任。我认为必须承认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容侵犯,故对均产之说与国家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喜欢,也不采纳。至于土地,原非人力所创的东西,乃上天赋予万民的财富,所以我也反对由少数人据为私有。本此道理,我主张恢复地权,以改变穷苦大众的困境。但怎样才可以实行呢?我以为言论宣传终难生效,唯有诉诸武力斗争一法。
呜呼!我的理想与现实,相距何止千里之遥。但又岂能仅以理想而自足,当更希望将它付诸实现。我以为世运的变迁,可于一朝之间,倒退百年之前;亦可于一夕之间,迈越百世之后。千里的距离,一瞬之间岂能一致?唯有靠武力,方能兴起;赖天人的和合与否,始可决定。但所谓武力,如果不能实际施行,亦不过一种梦想而已。我之所以希望选择“中国”作为我施展实力的根据地,实因那里地广人众,而革命之机,又迫在眉睫之故。由我取而代之,抑或使志同道合者代而为之,应照一切的理想以确定立国的基础,然后以此号令寰宇,则我的志愿或者可以实现吧!
但是,我又想到人不免有种族的偏见,所以打算先熟习那里的语言风俗,然后才潜入中国内地,并以“中国人”的身份来从事这番事业。但事与愿违,徒然浪迹于酷暑之地。后来得到木翁〔犬养毅〕的恩助,得入梦寐以求的乡土,遍访才俊之士,终于得遇孙逸仙先生。于是追随骥尾,奔走策划多年,其间或碰上菲岛事件,或在新加坡入狱,或受海峡殖民地和香港的放逐,或发生惠州起义、背山事件、同志内讧等等。我的事业,皆一败涂地。最后不得已而叩桃中轩之门,投身于浪花节界,与艺人为伍。我的理想结果成了梦想。
呜呼!云翁之言,陈白之诗,岂非对我已预作讽喻暗示?不过,我并不惋惜自己醒觉太晚。当我投身浪花节界时,实无勇气向知己前辈明言,因自己未能报答他们的恩义而竟落到如此地步,实深以为耻。这时偶然因事到弄鬼斋〔一木斋太郎〕处,恰巧麻翁〔神鞭知常〕亦来,同席畅饮。在谈话之中,这件事被麻翁察觉,他掷杯大声骂道:“太没有出息!我宁愿把酒泼在地上,也不能跟你这种人喝!”在酒力激动之下,我亦不顾礼貌,愤怒地说:“谁要你这样的庸俗政治家敬酒!”互相争论辩驳,由夕达旦。第二天,麻翁的门生来对我说道:“麻翁回家便卧床哭泣,屡次喊道:‘啊!就没有什么办法救救他吗?把他找来,把他找来!’”我听罢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啊!我的内心岂不痛苦!
后来木翁来一信谓:“昨天弄鬼子说你做了什么右卫门〔桃中轩云右卫门〕的徒弟,与念祭文曲的人为伍。我实在不胜惊讶。不过世间常有误传之事,但愿这是一个误传。”又谓:“日前筑前的三好将军来访,他近来效陶朱故事,经营商业。已非当年怒发冲冠的人物了。这倒是一件可喜的事。为什么独有你看破世事,挥锡杖于歌场呢?我实在不能明白。”对此,我实无词以对。
又过数日,一念〔古岛一雄〕兄来访,说:“木翁和他夫人嘱我劝阻你。也许你不高兴,不过,请你仔细考虑,能不能回心转意,还像从前那样,穿套外挂衣裙,去和他喝个痛快,何必杞人忧天呢?”我不答应。他潸然垂泪而去。啊!我的内心岂不痛苦!
我寄食于桃中轩家中后,有一天和老师同到云翁公馆,以实相告。翁微笑道:“做什么也没有关系。不过,难免有人要议论的。对,他们劝阻你我也赞成,你不听劝止,非干不可,我也赞成,双方我都赞成。说起来,在人生的舞台上,总得让你有一个角色呀!”啊,我的内心岂不痛苦!
我的新知旧雨中,或者面谈,或者来信,对我的决心表示同情,或者给以安慰和鼓励的也不在少数,这是我感激不尽的。不过,我投身于浪花节界,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有什么雄心大志,只不过是因性之所好而选择了这个职业吧,对那些同情我的朋友,我实在感到惭愧莫名。啊!可以说我活了三十三年才知道自己的本分!当我决心做浪花节演员时,囊空如洗,一筹莫展。于是便致函熊本的三浦女侠,说明实情,请她援助。女侠寄来我需要的东西,并且写道:“你还在精壮之年,何以如此消极?切望你能回心转意。敬候回音。附寄微意,聊作代步之资。”我含泪花了她寄来的钱,却辜负了她的厚意,而从事于新的职业。此事特别要记在这里,以表谢意。
啊!人世原是一场梦。“三十三年之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今公开作说梦的痴人,又岂能免贤者的一笑?
二哥不仅是我暗夜中的明灯,也是指示我一生进路的指南针。我们对宗教的见解相同,对社会的认识也一致。也就是说“要先给面包”这个意见,是我们一致的结论。但我在还来不及想出如何给面包的方法之前,便彷徨于恋爱的歧路上。这时,二哥却一直向前猛进,取得了最后的结论。他认为给面包的方法,古人业已道尽,社会改造论、土地处理法案等,均已陈腐。要之,实在于如何付诸实行,而实行之道,唯有靠“武力”一法。他观察社会的现状,担心俄国有一天会用野蛮的暴力,蹂躏人道,剥夺民权。因此,他主张为了维护民权必须依靠武力。也就是说,无论进而向世界广布人道,或者退而维护人权,武力的基础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务之急。那么在什么地方奠定这个基础呢?于是,他的夙愿——中国问题又复活了。他说:“人人都说中国国民是尊古的国民,所以不进步。这个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他们是以三代之治为政治的理想。三代之治的确是政治的最高标准,同我们的思想相近。他们之所以怀古,不正是为了大步前进吗?但是这个掌握政权已达三百年的朝廷,以愚民政策为治世的要诀,以致民困国危,终于自受其祸害,势将不能支持下去。这岂不是革命的大好时机吗?空谈理论究竟于世无益。愿我们能为共同的事业贡献此生,深入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念,思想当谋及百世,收揽英雄,以奠定‘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至于法国、美国那些稍重理想,希望建立某种主义的国家或不一定与我们为敌。我认为广泛地恢复人权,在宇宙中建立一个新纪元的方策,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听罢为之雀跃。这一席话解决了我一向的疑问,从而确立了我一生的根本方针。我们又商量了一些细节,最后决定先由我单身到中国去熟习语言风俗;二哥做好一切准备,随后再来。我又遵照二哥的意思,去和大哥商量,便从长崎返回故乡。
我回到故乡,见着大哥,详细地陈述了我和二哥商量的问题,并征求他的意见。在总的精神上他没有表示异议,但不同意我们的方法和手段。他说:“使中国人认识这种高明深远的道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又说:“假定这种事业可能成功,但是,梳发辫、穿华服、伪造姓名和国籍去讲理想,说这是为达到正义的目的而使用权术,则我决不敢苟同。假如要推行正义公道于天下,方法手段就必须光明正大。如果不依靠权术便不能实现志愿于世,那不做亦未尝不可。”我说:“志在于公而非私。成功则可救天下万世,失败亦甘愿一死。即使他人视为权术,于我亦问心无愧。”大哥说:“虽然,主张有时不能在一代中实现,若能公然向天下号召,百年之后当有人继其志而起。我宁愿这样等待。”我说:“议论世间已说腻了,自己的主张应该自己去实行,否则就等于百年以待黄河之清一样。”彼此意见背道而驰,不能统一。我便写信给二哥报告此事。因此二哥也回来面晤大哥,互相反复辩论,但终于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于是三人分为两条道路,各依其所信而行了。我和二哥未免因此稍感沮丧。但是二哥却安慰自己说:“我们的事业,本来不过是一种赌博而已。成功则奠定万世基础,失败则死同犬马。大哥的理想如宗教家之开基,虽不能立见功效,但是他所奉行的主张,在一定时期以后会发生效果的。假如不幸我们牺牲了,我们的精神还可由大哥发扬于世,正如一身有两体,更须奋励从事。”于是我亦稍微安定下来,激励自己一番,并愿意负起先行的任务;而二哥也希望我能早日启程。
我相信他说的话,便乘搭“西京号”轮船前往上海。航行两日,望见了吴淞的一角。水天相连,云陆相接,陆地仿佛浮在水上一般,这就是中国大陆!也就是我在梦寐中憧憬已久的第二故乡。轮船愈向港口前进,大陆风光愈益鲜明,我的感慨也愈益深切。我站在船头,瞻望低徊,不知什么缘故,竟然流下眼泪。
次晨早起,便驰往陈白寓所。见着那个和蔼的侍女,打听在否。她说:“还未起床,我去叫他起来。”我止住了她,在庭前徘徊,等他起床,独自陷入了妄想之中。忽听“吱嘎”开窗的声音,不由得抬头一望,见有一个身穿睡衣的绅士伸头向外探视,见到我便微微点首为礼,用英语说了一声“请进”。我仔细一看,这个人正是在照片上见过的孙逸仙先生。于是身施一礼,走进门去。被让到客厅落座以后,他也拉过一张椅子和我对坐。他刚刚起来,口未漱,脸也未洗,对他这种态度随便的样子,我首先感到惊讶,又觉得他有点轻率,不够稳重。我立即递过名片,道过初次见面的寒暄。他说从陈白那里已知道我的情况,并问我广东方面的情势如何。我说明无暇详查该地情势而回来的理由,并且告诉他今天能获见一面的喜悦。他复述了从陈白处已听到先二兄的事情以及我和陈白相识的经过。又说今天的相会是上天的安排,对我仿佛早已以心相许,毫无隔阂。这时我的喜悦可想而知了。但是对他的举止动作的轻忽,略失庄重之处,则不免感到有些失望。少时侍女来说漱口水准备好了,他说了声暂且失陪,便走出客厅去。这时我心中觉得有些迷惘,沉思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个人能够肩负起四百余州的命运吗?他能够身居四万万群众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究竟能否完成一生的志愿呢?的确,我正是以外貌来权衡豪杰与平庸。
我被硬石打伤,蛰居不忍池畔疗养时,孙先生来访,拿出一封信给我。我接过一看,是史坚如的噩耗。信中说:他在广东省城被官兵捕获,不久便牺牲于断头台上。呜呼,胡为至此?他年方弱冠,貌美如玉,温柔若处子,而抱忧天下之志,暗中与惠州革命军联系,只身潜入广东省城,进行放火,并向清督抚官邸投掷炸弹,炸死二十余人,令官员人等胆战心惊,为惠州革命军的进军顺利发挥了牵制清军的作用。以事泄被捕,终于被处斩首的极刑!
当我们在香港被逐回日本时,中日两国同志来送别的人很多,史君也来了。临别之时,吞宇以日本刀相赠。他很高兴地接过想要带走,因警官监视甚严,考虑了种种方法,终于把刀柄纳入长袖之中,把刀身藏在洋伞之内,连声呼妙,然后挥动右手,顾盼微笑,向我们作别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如见。如今其人已逝,悲夫!
惠州事件结束后数月,革命军败将郑弼臣﹝即郑士良,弼臣为其号﹞逃来。他已脱去满服而换上西装,剪掉发辫,散发披肩的外貌,宛如变了一个人,实令人不胜感慨。他又带来了一个噩耗,道:“当革命军开始攻打惠州城时,日本同志山田便前来投军协助。及至革命军将回三洲田时,竟失踪不见。实使人系念不已。”至今已两易星霜,依然杳无音信。他的命运,更令人不胜忧虑。山田居华多年,熟悉该国情况和形势,性温良而寡言,志高迈而热烈。当惠州事起,单身由上海驰往投效,由此可见其志气不凡。他究竟逍遥于如何的天地之中呢?但愿他仍在人间。
更多本书信息请登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网站:http:www.bbtpress.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