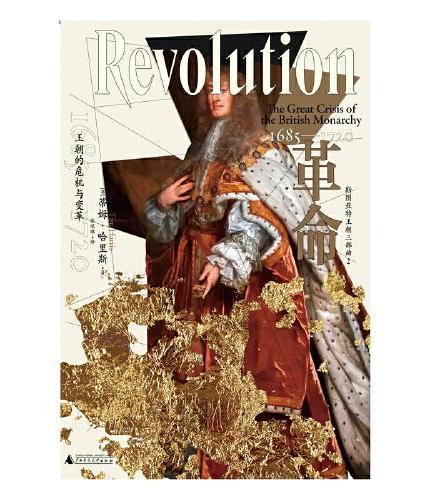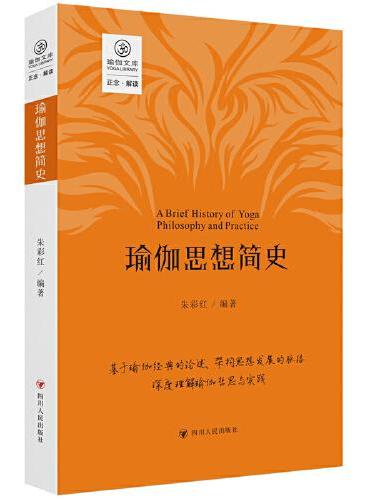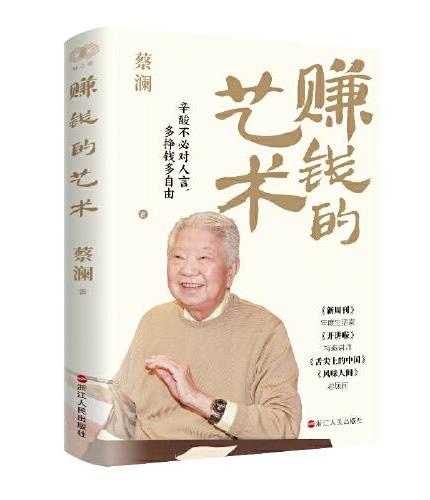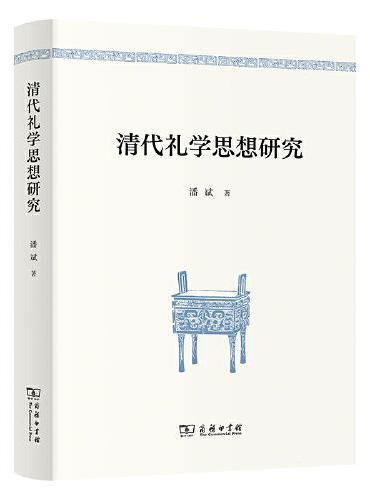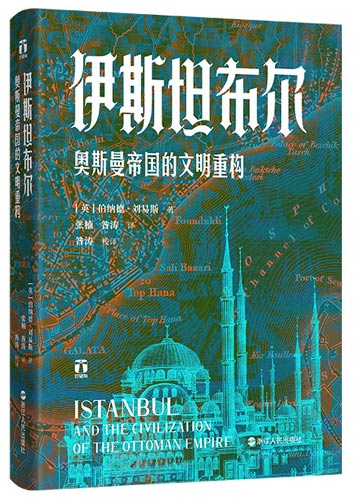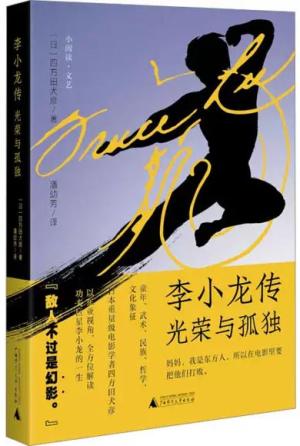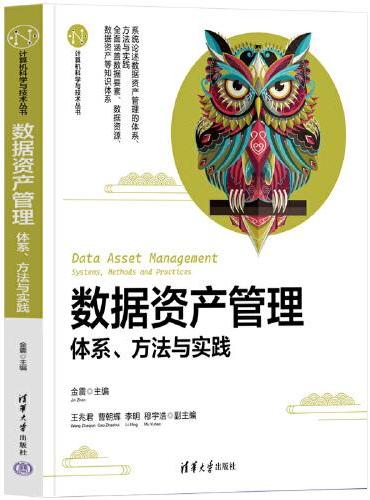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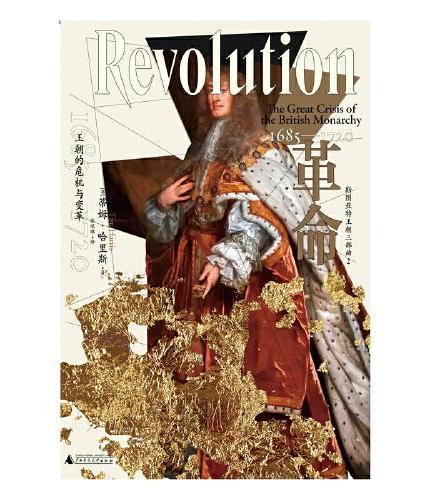
《
革命:王朝的危机与变革,1685—1720
》
售價:HK$
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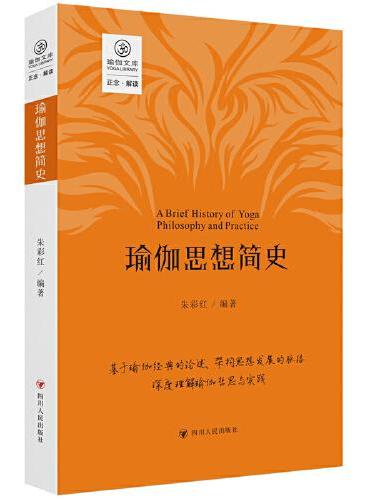
《
瑜伽思想简史(易于中国人理解的瑜伽思想发展脉络)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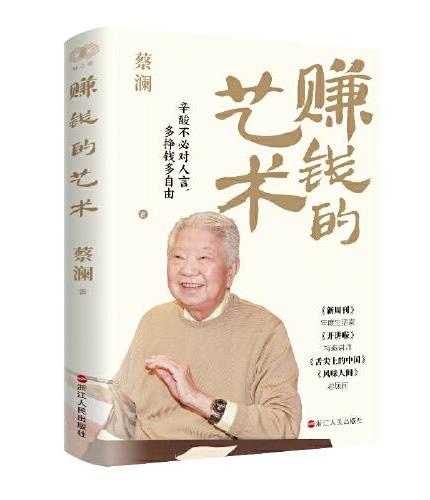
《
财之道丛书·赚钱的艺术
》
售價:HK$
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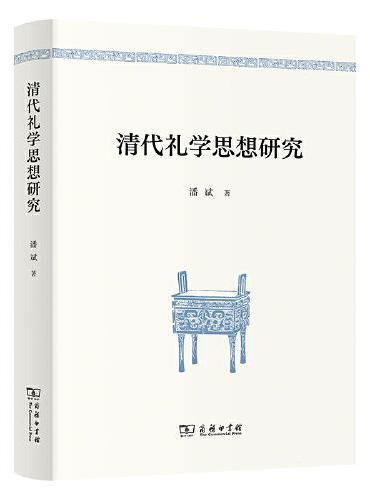
《
清代礼学思想研究
》
售價:HK$
98.9

《
赎罪
》
售價:HK$
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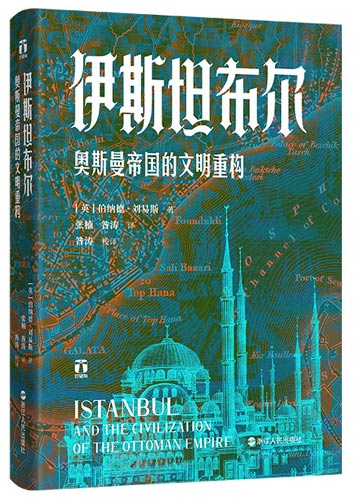
《
好望角丛书·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文明重构
》
售價:HK$
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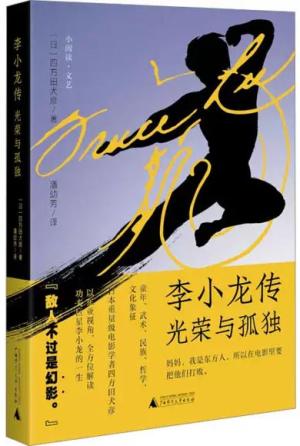
《
李小龙传:光荣与孤独
》
售價:HK$
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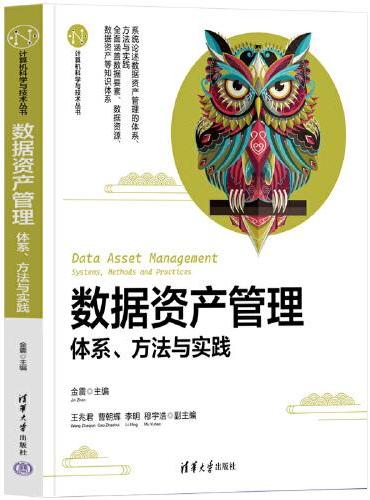
《
数据资产管理——体系、方法与实践
》
售價:HK$
90.9
|
| 編輯推薦: |
卡帕师从海明威,文字直接,幽默。
另本书附录卡帕在战场上拍的照片,具备珍藏和欣赏性。
|
| 內容簡介: |
《失焦:卡帕传》这本摄影手记,记录了卡帕追随盟军转战大西洋、北非、欧洲的经历及其四海为家的一生。
他用小说笔法记述自己的事情,文字直接、幽默,文风简洁明快。
卡帕的摄影,没有太多的色调、裁切的技巧讲究,他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是他全身心投身战地摄影的真实呈现。
《失焦:卡帕传》附录卡帕在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及二战等各个时期的摄影作品。
|
| 關於作者: |
罗伯特·卡帕(1913年10月22日-1954年5月25日),原名安德鲁·弗里德曼,匈牙利人,史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参与报道过五场二十世纪的主要战争: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二战欧洲战场,
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及第一次印支战争。二战期间,卡帕跟随美军报道了北非、意大利的军事行动,诺曼第登陆中的奥马哈海滩战役以及巴黎的解放。1954年5月25日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
张炽恒,诗人、文学翻译家,有多种经典文学译著在大陆和台湾出版。
|
| 目錄:
|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附录:卡帕摄影作品选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1942年夏
绝对没有必要再清早即起。我的工作室在第九大街一栋三层小楼的顶楼,整个屋顶被天窗占据,角落里放着一张大床,电话机搁在地板上。没有其他家具,连个钟也没有。阳光把我唤醒。我不知道时间是几点,也并不特别想知道。我身上的现金只剩下一枚五分镍币。电话铃不响,我便不想动弹,我等着人家来电请我吃顿饭,给我份工作,至少借给我一点钱。电话铃不肯响,我的肚子却叫了起来。我意识到,再想睡上一会儿那是没门儿了。
我翻了个身,看见了女房东从门底下塞进来的三封信。最近几个礼拜只有电话公司和供电局给我来信,因此,那神秘的第三封信终于把我请下了床。
果然,一封信是爱迪生联合电信公司来的。第二封信来自司法部,通知我说,我,罗伯特?卡帕,前匈牙利人,现无明确身份人士,据此而被划归为潜在敌侨,因此必须交出照相机、双筒望远镜和轻武器,如果要外出离开纽约超过10英里,必须提出申请,获得特批。第三封信是《
柯里尔 》杂志①的编辑写来的,他说,对我的剪贴簿经过两个月的研究之后,《 柯里尔
》杂志突然确信我是一个了不起的战地摄影师,非常乐意派我去担当一项特殊任务;他们为我在一艘四十八小时后开往英国的船上预订到了一个舱位;信中附有一张一千五百美金的支票,作为预付薪酬。
这其中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有打字机,有足够的勇气,便会给《 柯里尔
》杂志回信,告诉他们:我是敌侨,连去新泽西州都不行,更不必说去英国了,我带上照相机唯一能去的地方是市政厅那边的“敌侨财产处置所”。
我没有打字机,但口袋里有一枚镍币。我决定掷硬币。如果掷出个字,就设法逃之夭夭,去英国;如果掷出个背,就把支票退回去,向《 柯里尔
》杂志说明情况。
硬币掷了出去,是个背!
但接着我意识到,一枚硬币里是没有前途的,我会收下支票,把它兑换成现金,无论如何,我会去英国。
————
镍币交给了地铁。支票交给了银行。我在银行隔壁的詹森餐厅吃了早饭,真是大吃一顿,花掉了两块五。这样一来事情就定了。我总不能还给《
柯里尔 》杂志一千四百九十七块五毛,而《 柯里尔 》杂志肯定算是麻烦上身了。
我重读了他们的信,确定我的船在48小时后起航。我又重读了司法部的信,琢磨着从什么地方下手。我所需要的一切是:征兵局的豁免,国务院和司法部的出境和再入境许可,英国签证,还有办签证要用的某种护照。一开始就碰钉子我可担待不起,所以我得先找个听得进去的地方开口。我有麻烦。嗯,美国才刚开始知道麻烦的滋味,而英国已经打了两年多的仗,对这种滋味应该已经是熟知了。我决定先去找英国人。
从詹森餐厅到航班终点站步行五分钟就到了。我得知不到一小时后就有一班飞机飞往华盛顿。我买了一张票,《 柯里尔
》杂志的钱又少了一些。
两个半小时后,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我要求见新闻专员。他们带我去见了一位穿粗花呢衣服的先生,那人脸膛很红,神情很厌倦。我报上姓名,但不知从何说起,因此我简而化之,把两封信给他看,先是《
柯里尔
》杂志的,然后是司法部的。第一封信读下来,他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当他把第二封信放下来时,他的唇边露出了一丝笑意。我多多少少受了点鼓舞,掏出爱迪生联合电信公司寄来的那封尚未开拆的信,递给了他;我清楚得很,那是通知我,要断我的电了。他示意我坐下。
想不到,他一开口便人情味十足。战前他是地质学教授。战端初起之时,他人在墨西哥,正快乐地研究休眠火山山顶的土壤成分。他对政治并没有多大兴趣,但这是战争,他应召而去,成了新闻官员。从此以后,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利益,他不得不拒绝种种提议和要求。他安慰我说,我这件事非同一般。我排到了头号!对他、对我自己的同情令我大动。我提议共进午餐。
我们去了卡尔顿餐馆,等座位的时候,我们百无聊赖,喝了许多干马提尼酒。我的同伴已经相当兴奋,而我也开始感到,那位大使馆专员和大英帝国,连同《
柯里尔
》杂志,将和我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们终于等到了一张桌子,我拿起菜单,先点了每份一打的蓝点牡蛎①。五年前,在法国,我在饮酒方面可是下了很大本钱的。我记得,每一篇英国神秘小说中,每当彼得?温西爵士有话要说时,吃牡蛎总是佐以那种名叫Montrachet的勃艮第白葡萄酒②。1921年产的Montrachet在单子的末尾,价格昂贵。这是个快乐的选择。同伴告诉我,十五年前,他在法国度蜜月时,就是用这种酒让他的新娘大为动容。因此,当那瓶酒喝到底的时候,话题已经变成我们对于法国和Montrachet的爱好了。喝完第二瓶之后,我们一致同意,在把德国人扔出la
belle③法兰西这一点上,我们的情感同样强烈。喝完咖啡加Carlos
Primero白兰地④之后,我给他讲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我在共和军里的三年经历,以及我为何有充足的理由恨纳粹。
回到大使馆后,他拿起电话,要通了政府部门。他越级找到了某个高层人士,直呼其名,说他的办公室里有个“好人老卡帕”,说我去英国这件事重要之极,我会在十五分钟后过去拿我的出境和再入境许可证。他挂上电话,给我一片纸,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十五分钟后我到了国务院。一位衣着端正得体的先生接待了我,他在一份表格里填上我的姓名和职业,签了名,告诉我明天早晨九点,去位于纽约港斯塔腾岛区①的移民局办事处,一切都会办妥。然后他陪我走到门口,这一会儿,他变得很随和,拍拍我的背,朝我使了个眼色,祝我“好运!”
我回到大使馆的时候,我的专员朋友有点严肃,还有点着急,我赶快告诉他,我的第一步成功了。这一次他打电话的对象是英国驻纽约总领事。他对他说,“老卡帕”要去英国,绝对一切都妥当,就是没有护照。又打了几通电话之后,也就是过了十分钟吧,大使馆的海军专员、教授和我,已经在一家小酒吧里喝酒祝贺我出行成功。我去赶飞机的时间到了,但在分手之前,海军专员向我保证,他会给联合王国①的每一个港口发电报,说我将乘船抵达,随身带着相机和胶片,让他们在各方面帮助我,把我安全地送到伦敦的海军部。
回纽约的飞机上,我断定英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幽默感,碰到过不去的坎儿时,他们是好帮手。
————
第二天早晨,英国驻纽约总领事说,我这件事极不寻常——不过战争也极不寻常。他给我一张样子很普通的白纸,要我写下我的名字,解释一下我为何没有护照,说明我的旅行缘由。
我写道,我名叫罗伯特?卡帕,出生于布达佩斯,海军上将冯?霍尔蒂②和匈牙利政府一向不喜欢我,我也一向不喜欢他们;自从希特勒合并匈牙利之后,匈牙利使馆便既不承认我不是匈牙利人,又不承认我是匈牙利人;既然是希特勒在管着匈牙利,我便干脆不承认我是匈牙利人。按出生而论,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犹太人,我痛恨纳粹,觉得我拍的照片可以用作反纳粹宣传品。
把那张纸递还给他时,我稍稍有些担心自己有没有拼错词,但他加了印,盖了章,周遭绕上一根蓝丝带,一本护照便诞生了。
————
当天上午我便要上船,但还有四五项小的许可证要办。我母亲当时住在纽约,她陪伴着我;我去弄必需的最后那几张盖章纸片时,她坐在出租车里等我。我每一次回到车里时,她都静静地坐着,想从我脸上看出结果如何。她是一位伤透了心的母亲,为了我如愿,她希望我把各种许可证弄到手,顺利地成行;而以她的母爱之心,她却暗中希望出点什么岔子,使我无法离开她再去战场。
最终我得到了所有的许可证,但此时,我那艘船的预定开船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我母亲仅余的希望是:船已经开走。
但是我们到达码头时,那艘脏兮兮的旧商船还在那儿没走。一个大块头爱尔兰裔警察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给他看证件。
“你迟到了,”他说:“你最好麻利些。”
到此我母亲必须止步了。她不再代表“战争时期的勇敢母性”,而是化作了一颗宽容和充满爱的犹太人的心。从她那大而美丽的棕色眼睛的眼角,积蓄和压抑已久的泪水泉涌而出。六英尺六高的爱尔兰裔警察用胳膊搂住我那五英尺高的小个子母亲的肩膀,说道:“夫人,我去给你买杯喝的。”
我向着母亲飞了最后一个吻,向船的跳板走去。
我看美国的最后一眼,是爱尔兰裔警察和我母亲的背影,穿过马路,走向突然露出笑颜的摩天大楼脚下那间小酒吧。
第二章
我赶紧上了跳板。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晚到的人。紧跟着两个摇摇晃晃的水手的脚踵,我大踏步走出了美国。
船长站在跳板另一头,转过身来对他的手下说道:“嗯,最后两个了,回去歇着吧。”接着他看到了我:“你是谁?”
“我是个比较特殊的乘客,先生。我是那个去旅行的敌侨。”
“嗯,我们捎上了一样奇怪的货物。我们不妨下去,到我的船舱里,看看载货单上你的情况。”
他发现我正式列在载货单上,浏览了一遍我的证明文件,没有加以评论。
“战前,”他告诉我:“我从西印度群岛向英国运香蕉和旅客。现在可不是运香蕉了,而是往回运熏肉,旅客散步的甲板上装的也不是人了,而是分拆开来的炸弹。嗯,我的船不像往常那样整洁了,卡帕先生,但是我的客舱都空着,我想,你会发觉自己的住处很舒坦的。”
我找到了自己的船舱,安顿了下来。引擎在嗡嗡地叫。在美国待了两年之后,我又上了回欧洲去的路。我的思绪不知不觉中回到了过去……两年前,我乘飞机从法国出发,抵达的也是这个港口,当年,我不得不为他们是否会让我入境而担忧。当年,我持有的证件也是纯粹临时现编现造的。我被描述成一位农业专家,途经美国去智利,去为该国改进农业标准,持有过境签证,获准在美国逗留三十天。当时好不容易登岸……好不容易说服他们让我留下……而今却多亏了一位英国教授创造的奇迹,我才得以离开……
我取出了照相机,从1941年12月8日起,我连碰也不曾有机会碰它一下——给自己倒上一杯之后,我便又成了新闻记者。
————
拂晓时分,我们在哈利法克斯港①抛了锚。船长在此地上岸,去接受指令。这天晚些时候,他回来之后,我获悉,我们将参与组成一个牢固的护卫舰队,横跨大洋;我们这条船将充当领头舰;一位退役海军上校担任护卫舰队司令官,他将从我们的舰桥上发号施令。
我在《 柯里尔
》杂志上看到过一篇四页篇幅的感人文章,题为“护卫舰队司令官”,并附有几张生动的照片,只见那位年老蹒跚的老水手站在舰桥上,一条条船在海上颠簸着。
晚饭过后,司令官派人来叫我。舰桥上黑乎乎的,但是当我辨认出他的模样时,我失望了。我看到的不是我拍过照片的那位年老蹒跚的海上雄狮,而是一位五十多岁、衣冠整齐的绅士,在他与我所想象的人物之间,我能找到的唯一类同之处是:一副又粗又浓的眉毛。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回应道,要说他本人,他是爱尔兰人。他立刻话锋一转,紧接着说道,他对电影世界很感兴趣,发现好莱坞有些女演员相当令人激动。整个航程中,他都必须待在舰桥上,我何妨每天夜间上来,给他讲些好莱坞的美好故事?作为交换,他很乐意给我讲讲护卫舰队的种种事情。
这项交易相当不公平。因为司令官了解他的护卫舰队,而我却从未去过好莱坞。但我没有心情对他说,他把我的名字的音发错了,说我不是那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我的名字是鲍伯?卡帕,根本不是弗兰克?卡普拉①。在这次航程的剩余时间里,我将不得不扮演山鲁佐德②。我只有巴望不会延续一千零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我们在港湾里度过。第二天早晨,司令官问我是否乐意随他去拜访护卫舰队各艘船舰的船长。我们大部分船都是挂着外国旗航行的,司令官费了很大工夫,好不容易才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瑞典船和挪威船的船长向我们敬了威士忌,并且说一口相当好的英语。荷兰人奉上的是上等的杜松子酒,交流起来也毫无困难。法国船长的酒是很醇的白兰地,我给他们当翻译。希腊人的酒凶得要命,名叫茴香烈酒,船长把希腊语说得飞快。我们总共拜访了二十三条船,总共喝了二十三个不同民族的酒。回自己船的路上,司令官把所有那些疯狂的外国人抱怨了一通,使我觉得自己倒是个纯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①了。
下午我们毫不费事地把护卫舰队编组了起来。我们排成四排,每排六条船,各排之间相距一千码。我们的护卫力量可以说很不济,只有一艘驱逐舰,再加五条很小的轻型巡洋舰。
舰桥上的第一晚,是司令官当的主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过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到了1918年,他已经在指挥一个整编小舰队了。泽布拉格②和加利波利③这些地名在空中乱飞。故事讲完之后,他问我,莉莲?吉什④近来好不好。我让他放心,吉什小姐的状况仍然良好。分手之际,一段美好的友谊似乎已经开始了。
海上的最初四天平淡无奇地过去了。白天我拍照,拍每个人,每一样东西,从桅顶拍到轮机舱;晚上我到舰桥上去,把我在牙科诊所的候诊室里读过的影迷杂志上的内容,能记起来的,都讲给司令官听。我隐隐约约地暗示他,我是个很谨慎的人,但仍然让他觉得,那些好莱坞丑闻中,多少也有我本人的份。作为交换,他给我讲,那一次,他的一个护卫舰队去摩尔曼斯克①,途中他的靴子在甲板上冻住了,他如何三天时间动弹不得。在远海上司令官不喝酒,而我却在口袋里放着一瓶酒,在他神侃时借酒御寒。午夜过后,我倚靠在舰桥的围栏上,有时会觉得自己身在第三大道②一间熄了灯的酒吧里。
迄今为止,我的“北大西洋战役”完全是一件乐事——说实在的,太快乐了。不过,船员们对我渴望行动这一点不屑一顾,并且根本不在乎《
柯里尔 》杂志上的故事有可能很单调乏味。
第五天,我们遇上了真正的北大西洋大雾。我们的驱逐舰靠拢来,在船队旁边行驶,并用灯光给我们打信号。司令官转身对我说道,“卡帕,如果你能在雾中拍照,你就能终究搞到你那该死的独家新闻了,”他说道:“一个德国潜艇群正埋伏在前方三十英里处等着我们。
有雾与否,司令官都断定我们必须改变航线。这时,我们从舰桥上都看不到自己的船艉,我们还必须最严格地断绝无线电通讯。与护卫舰队其他船只之间,只得通过浓雾信号来联系。挪威人的油轮原先在我们左侧行驶,此时却从右方某处发出两长三短的汽笛声来回应我们。希腊货船本来行驶在船队末尾,在我们后面大约三英里,却从距我们这一排五十码的地方发来它那接连四长的汽笛声。总而言之,二十三艘船舰的雾号所形成的声浪,足以传到柏林。司令官咒骂着所有同盟国、中立国以及战时盟国的船长。但是没时间去担心撞船事故。潜艇群已经发现我们,我们的护卫舰正在丢深水炸弹。
我用防水的丝绸烟草袋把宝贵的护照和剩余的《 柯里尔 》杂志的钱包好,对于我这段故事的进展感到悔恨万分。
司令官发出信号,要船队分散开来,从此时起,每一艘船都各自为政。我们不时听到其他船的引擎声很难听地在近处响起,但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远。
四十八小时之后,灿烂的阳光刺透了浓雾。二十三艘船全在我们周围。连我们的护卫舰也在。事实上,我们仍然成一个编队,只是原先在船队中央的船现在行驶在外围;原先在最后的希腊船,现在跑在最前面,而我们却拉在了船队末尾。
一个小黑点出现在地平线上,不多一会儿,它便开始发闪光信号。我们的信号员脸上完全不带表情地把信息转告我们:“长官,H.M.S.哈维斯特号询问,你是否可以分给他们一些啤酒。”
“叫他们过来拿。”
驱逐舰绕着船队转了一两个花哨的圈子之后,欢快地冒着蒸汽赶上来,与我们并排行驶。英国驱逐舰舰长手持扩音器站在舰桥上:“见到你们真惊讶,长官,你们这些船竟然都还漂着。”
“很惊讶见到英国海军漂着——却没有啤酒!”
“我们的深水炸弹用完了,只好向他们扔啤酒桶,草草了事!”
————
不久,一串对我来说不可解的旗子升上了我们船的桅杆。信号员为我翻译了旗语:“很自豪从后面领导你们,不过还是请恢复原始队形。小心些。”
各船发出收到信号。挪威油轮撞到了希腊货船;那位瑞典绅士全速向后退去,不久便从视野中消失了;法国人报告说,因为锅炉爆裂,他们只好掉在后面了。经过四小时的来回打转之后,船队以二十二艘船的编制继续行进。
那天晚上,我在舰桥上与司令官会合时,他有一会儿没搭理我,正当我准备回舱去时,他挪了挪窝:“顺便问一声,卡普拉,你有没有见过克拉拉?鲍①?”
————
结果,驱逐舰白白浪费了啤酒,因为第二天,德国潜艇又出现在我们周围。我们的驱逐舰在船队四周施放了一道非常上镜头的烟雾,并用无线电发出了求救信息。有一艘英国驱逐舰本应在此时与我们会合,很幸运,它如约而至。作为《
柯里尔
》杂志“北大西洋战役”的收尾之笔,在一艘德国飞艇和一艘桑德兰号英国驱逐舰之间,发生了好一场混战,并且我们整个船队的每一架高射炮都参与助战,喷射出一股股的黑烟。
我把照片都拍了下来,当爱尔兰海峡的灯塔映入眼帘时,我的想象力早已被好莱坞的故事吸干。
司令官去下面了,这可是头一遭,我被他丢在舰桥上,和他的信号员一起待着。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整个航程中,没有说过一个多余的字。他先看仔细司令官确实离开了,然后才对我耳语道:“老头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但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嗯,他给讲的那些故事中,有些……”
他这样一说,我感觉好多了,但我下定决心,一有机会,我就向弗兰克?卡普拉太太道歉。
————
进入海峡时,我们改变了队形,各船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了一百码。于是,无线电第一次打破了沉默,各船分别得到了在何处停泊的通知。我希望我们的船在利物浦靠岸,开始安排我在伦敦萨伏伊饭店①第一天的日程。但战船管理部尚未开始运行,我们接到命令,驶向爱尔兰海,在贝尔法斯特②港口外等候下一步指示。
萨伏伊饭店得有二十四小时生活中没有我。司令官对我说,那并不太坏,他知道在贝尔法斯特住哪家客栈合适,并且,对于他来说,他要补充大量储备!
我们抛锚后不久,一艘摩托艇驶了过来,几位戴常礼帽的先生,移民局的,登上了我们的船。轮到检验我时,那些先生们全神贯注地查阅我的证明文件。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摇晃他们那戴着常礼帽的脑袋,一点满意的神情也没有表露出来。当他们得知我有照相机和胶片时,他们的常礼帽摇得更起劲了。我提到华盛顿大使馆专员发的电报,但他们听在耳朵里,脸上一点反应也没有。绝望之余,我想逗个乐子,便说我真的不是赫斯先生①,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吊在降落伞上登陆英国。但他们并没有被逗乐。他们对我说,特此告知,战争期间,只有联合王国的公民才允许在北爱尔兰登岸。我只能待在船上,直到我们的船在英国某适当的港口停泊为止。政府当局会决定我的命运。
抛下我,司令官似乎真的于心不忍。他把自己的船舱让给我,言之凿凿地对我说,我给他讲的故事是最有趣的,然后便同移民局官员一起上了岸。现在,船长又重新全权控制了他的船,他想安慰我,便说,在外面待上三天之后,他会接到继续向伦敦前进的命令。他欢快地补充道,鉴于我们尚未正式停泊,船上的商店仍然会开着,苏格兰威士忌仍然以每五分之一加仑七先令的价格供应。
我搬进了司令官的船舱,叫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第一无线电操作员坐下来玩二十一点。晚上十点钟,酒瓶空了,《 柯里尔
》杂志的钱输掉了150美元。我又叫了一瓶酒,但乘务员两手空空而归,神情很奇怪地看着我,说他们叫我去船长的舱房。
我踉踉跄跄地上了舰桥,心头大难临头的感觉不轻,肚子里苏格兰威士忌则是灌得太多太多了。我看清了和船长一起的是两位年轻的海军军官。他们的名字是加别吉和米勒,确认过我名叫卡帕之后,他们要求我把照相机、胶片和笔记交给他们保管。我对他们说,不行,这可不行。我可离不开我的照相机、胶片和笔记。此外,我补充道,说好了我到达时英国海军会给我种种便利,而到目前为止,我什么便利都没得到,一样便利都没得到。相反,我被无礼地撂在一艘空船上,漂在爱尔兰海中央。如今我还得待在船上,有朝一日我到了英国,一定会好好地控诉一番。
他们俩嘴巴里嘟囔着现在是战争时期什么的,退到一个角落里,研究起一张神秘的纸片来。他们商议了几分钟,把那张纸反反复复看了至少三遍,然后转过身来,坚持要我马上交出照相机、胶片和笔记。这是一种新调门,我很不喜欢。
突然之间,透过苏格兰威士忌的迷雾,我把一切都看清楚了。我把他们合二为一,向他们表示,我说得出那张纸片上的内容。我跟他们讲,华盛顿的海军专员如何说要给联合王国的每个港口发一份电报,说明有一位罗伯特?卡帕会带着照相机和胶片乘船抵达,对此人和他的照相机和胶片要照顾好,要彬彬有礼地予以帮助,把他送到伦敦的海军部。现在他们只要回去,与驻华盛顿大使馆核实一下,告诉海军部,我就在这条船上,将于某个时候靠岸,就行了。
加别吉和米勒看看那张纸,又互相看看,然后把它递给了我。一点都没错,上面说到了胶片,照相机和卡帕,但那上面又反反复复加了编码,倒可以像圣经一样,加上许许多多的阐释了。加别吉一下子变得温和谦恭起来,问我是否可以和我私下里谈一谈。
“我们肯定你说的没错,先生。”他犹犹豫豫地说道:“希望你信任我们,相信我下面要说的话。”
我很高兴情势发生了扭转,听他说下去。
他解释道,他和米勒在贝尔法斯特海军情报部门工作,白天的任务弄得他们精疲力竭,下班后他们便去喝一杯。他们在酒吧里遇上了一艘扫雷艇的艇长,他们是多年前的老同学,他劝他们去他的船上看看,因为船上的酒比酒吧里便宜得多。果然,那儿的酒又便宜又丰富,弄得他们不久前才找回自己的办公室。就是那一会儿,他们发现了这份电报。现在,如果他们两手空空回到海军情报部门,就得被迫承认这种多少有些特殊的情形耽误了他们。如果我不帮他们,他们就会陷入最可怕的困境之中。加别吉接着说道,如果我随他们上岸,他们一定会帮我,带着我的照相机、胶片等一切,通过最好的途径,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伦敦。
发点善心并不是件难事,我决定帮助英国海军。我从商店里买了三瓶威士忌随身带上,随加别吉和米勒而去。在一团漆黑之中,我们爬下一段摇摇晃晃的绳梯,上了一艘小得不能再小的摩托艇——它正不耐烦地上下颠簸着呢,它驶了出去。
可是我们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驾驶员回过头来告知我的两个朋友,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钟,海关和移民局要到早晨八点钟才开门。无论如何他不能送我上岸!
我们三个变得沮丧之极,不过这一次米勒解了围:“我看还是去找扫雷艇吧。我们可以在艇上舒舒服服地过一夜,早上再乘摩托艇进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