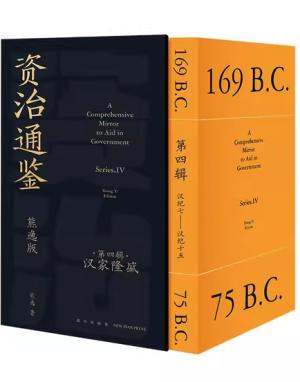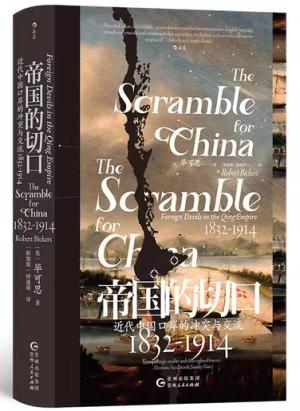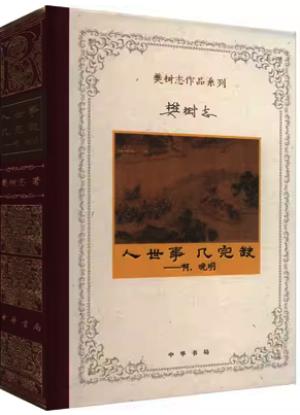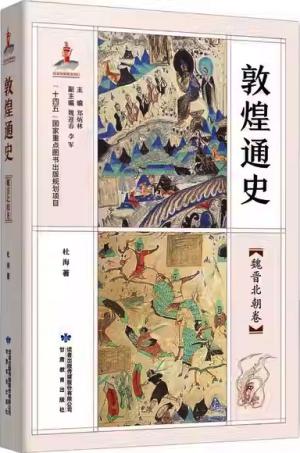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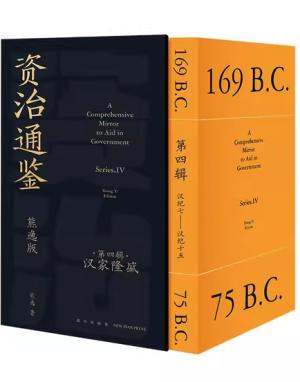
《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
》
售價:HK$
470.8

《
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项维仁:工笔侍女作品精选
》
售價:HK$
66.1

《
宋瑞驻村日记(2012-2022)
》
售價:HK$
1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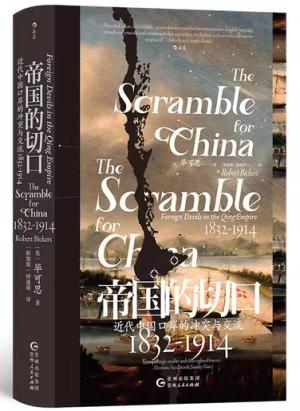
《
汗青堂丛书138·帝国的切口: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1832-1914)
》
售價:HK$
1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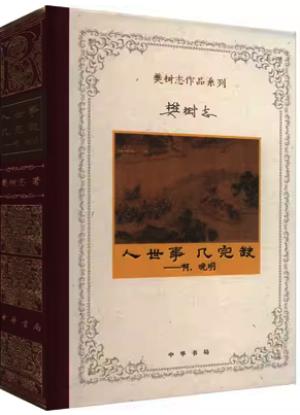
《
人世事,几完缺 —— 啊,晚明
》
售價:HK$
115.6

《
樊树志作品:重写明晚史系列(全6册 崇祯传+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明史十二讲+图文中国史+万历传+国史十六讲修订版)
》
售價:HK$
498.0

《
真谛全集(共6册)
》
售價:HK$
11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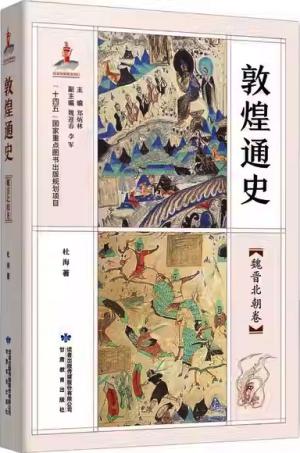
《
敦煌通史:魏晋北朝卷
》
售價:HK$
162.3
|
| 編輯推薦: |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足球队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展现国破家亡之际中国足球在亚洲球王李惠堂的带领下战绩斐然,在亚洲所向披靡。
★小说双男主双线叙述,对小北来说,从乞丐到球队主力,《为国争》是坎坷进阶之路;对余伯庸来说,从唯利是图到舍身成仁,无赖也有为国争之义。
★刺激的赛事 激烈的战事 悲壮的国事,市井庸人的荆棘成仁之路。
★余耕向自己体育生涯致敬之作,上“场”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英雄。
|
| 內容簡介: |
余伯庸在赌桌上输掉球队的比赛经费时,小北在街头乞讨,居无定所。
小北以替补队员身份上场踢进决胜球时,余伯庸被球队开除不知所踪。
余伯庸投机取巧大发国难财时,小北及球员们放下足球奔赴前线杀敌。
侵略者输球后怒将枪口对准小北及球员们时,余伯庸……他这次选择搅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
|
| 關於作者: |
|
余耕,早年从事专业篮球训练,后转行在北京做记者十余年。自不惑之年开始职业写作,先后创作长篇小说《金枝玉叶》《做局人》《最后的地平线》;中篇小说《我是夏始之》获得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如果没有明天》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根据该小说《如果没有明天》改编的话剧《我是余欢水》在全国各地上演500余场,改编成网剧《我是余欢水》成为现象级短剧。
|
| 內容試閱:
|
一
余伯庸把手伸进西裤,捣弄了一会儿,赌牌九坐了一整晚,内裤在裤裆里被两片屁股拧成麻花状,命根子处更是极不爽利。他挎着印有“中华足球队”字样的公文皮包,系好西裤皮带,杵在三元宝局门口打了通呵欠。接着,他一只手举起公文皮包,冲着从玲珑塔罅隙透过的霞光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整个人才感觉舒坦起来。最近运气真的是糟透了,到处都是用钱的窟窿,他却是赌啥赔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出门遇尼姑,十赌有九输。中华足球队搬到广州师范学堂训练,足球场北侧便是慈慧庵的正门,余伯庸一抬头就能看见进出化缘作法的尼姑。他最近的十次赌局输了九回,麻将、摇宝、牌九、赛马、彩票、抢场、十点半、十三张、回力球、斗蟋蟀……一一试过,全都输到底儿掉。烦闷无处发泄,余伯庸把输钱的恼恨全都归罪于慈慧庵的尼姑。
昨晚八时进了三元宝局,赌到今晨六点,五百块钱输得一个子儿不剩。这笔钱是体育部发放给中华足球队的比赛经费,用于半月后即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经过层层申请,体育部才给中华足球队批了两千大洋。领到这笔巨款的当天,余伯庸便将一千五百块钱挪作他用,支付他欠英国一家洋行的全部货款。整支足球队来回马尼拉的船票,加上食宿等费用,两千块钱得节省着才够开销。如今只剩下五百块钱,这该如何向李惠堂交差?中华足球队队长李惠堂,远东球王声名远扬,且余伯庸深知李惠堂疾恶如仇的秉性,此事绝不敢让他知晓。于是,余伯庸斗胆决定铤而走险,带着剩下的五百块钱进了三元宝局,他想去碰碰麻将运气,把那一千五百块钱赢回来。事与愿违,越是怕输越是输,牌桌上鏖战一夜,把剩下的五百块钱也输个干干净净。
余伯庸拖着肥重的身躯,一摇一晃挪下三元宝局的九级石阶,却见一道黑影从身侧袭来,劈手夺过他手中印有“中华足球队”字样的皮包,撒腿便往前蹿去。余伯庸望着那人的背影,长舒一口气,装模作样地边追边用东北味儿广东白话大声叫嚷:“抢劫了,抢劫了……我丢你老母!”
余伯庸话音未落,身前闪出个一头乱发的年轻乞丐,操着满口西北腔,问道:“我把包追回来,你给我二十块钱?”
余伯庸瞅了一眼劫匪奔逃方向,背影早已消失在路口,估摸着眼前这个乞丐肯定追不上,便点了点头。余伯庸再抬首时,年轻乞丐已经奔出去足有十米远,地上的木棉树落叶都被他的脚风带起来,飞旋在他足间,浑似在助其脚力。余伯庸愣怔怔地看着年轻乞丐在路口消失,不可思议地摇了摇肥硕的脑袋,转身逆向而去,他要去沙面的莲香楼吃早茶。
能讲一口流利白话的余伯庸是东北人,二十一岁那年跟他的双胞胎哥哥一起考进教会燕京大学,一时间成了余家屯子里最有出息的孩子。屯子里都说余家祖上积德,两个儿子都走出余家屯子读大学。余伯庸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对屯子里围绕着他的半大小子们说道:“别听你们爹娘胡咧咧,我昨天还是他们嘴里的操蛋熊孩子。”
余伯庸的确是个操蛋熊孩子,不像他哥哥那样老成持重受父母宠爱。余伯庸十二岁那年,村子里的私塾被日本人关闭了,他成了野孩子王,某日屯子里十几个土蛋狗剩小豆子啸聚一起,抢劫了一个货郎。货郎寻到余家屯子告状,屯子里的人一齐指向余伯庸家。余父从存放稻谷的大缸里揪出余伯庸,当着货郎的面把儿子吊起来毒打一顿,一直打到货郎和哥哥余伯平出手阻拦才罢手。余父对着货郎好言好语赔礼道歉,又从二姨太太的梳妆匣里强行夺来两块现大洋,才把货郎打发走。私塾关闭没几天,日本人开了新学,日语成了新学的主要课程。余伯庸刚刚疯了没几天,跟哥哥一起又被关进管理更为严苛的日本人的学校,这才算把他的野性收敛许多。
从余伯庸的祖爷爷开始,余家便是余家屯子的富庶大户,遭人羡慕嫉妒了好几代。祖产传到余伯庸他爹时,家底已大不如前。余父好赌乐嫖,既不喜务农又不善营商,混不到晚年便有些入不敷出。几经变卖房产、耕地,勉强支撑一家人过活,好在余家两个儿子余伯平和余伯庸双双考入燕京大学,为余家在余家屯子争回些颜面。可惜好景不长,三年后的寒假,余伯庸跟随同学去了广州游玩,余伯平独自一人返回东北老家过年,大年初一说是出门拜年,结果再也没有回来过。被全家人寄予厚望的余伯平销声匿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了余家的一个谜团,更成了余家屯子茶余饭后的谈资。余父曾经逼问过余伯庸,询问老大余伯平去了哪里。余伯庸一脸懊恼,说大哥是放寒假在家里失踪的,他在广州如何知道?余家上下还沉浸在两个儿子考入燕京大学的喜悦中,接着又迎来余伯平离奇失踪的悲苦,余父整日里感叹人生无常、福祸相依。余父甚至觉得福祸是个玄学,既是个人的命数,也是家族的劫数。
余伯庸在教会燕京大学读到第四年的寒假,回到余家屯子陪着父母过了最后一个年。开春后,余伯庸没有回学校,而是给父亲留下一封信,声称自己厌倦了读书,要去天津做生意,随后便拎着一只小行李箱只身去了天津。在天津混了一年之后,余伯庸继续南下去了广州。一个北方人到了南粤,压根儿听不懂白话,就算是给人家打零工也顶多混个饱肚子。好在余伯庸目的性强,他只去洋行打工。洋行都是跟外国人做生意,需要会讲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余伯庸靠着他的语言天赋,渐渐在广州站住了脚。只六年,余伯庸便坐上了泰和生洋行的经理职位。泰和生是一家专门与德国人从事贸易的商行,经营常规的茶叶、丝绸、陶瓷,有时甚至还夹带小规模的枪支弹药。泰和生的老板是个胆小之人,他告诫余伯庸不要碰军火生意,不要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可一心想做大生意赚大钱的余伯庸,丝毫不把老板的忠告当回事,最终被人告发,锒铛入狱两年。
等他出狱后,已经没有洋行敢招他入伙。天无绝人之路,这余伯庸攀上了球王李惠堂的关系,摇身一变成了中华足球队的经纪人。
二
年轻乞丐叫小北,但这个时候他还不叫小北。小北本来没有名字,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也就无从起名字。小北记事的时候,身边只有娘。娘带着他从冰天雪地一路往南走,说是南方暖和,不会把手和脚冻伤裂口。他爹念叨了一辈子要带老婆去南方见见世面,可直到他爹死时,他娘也没走出过童家堡子。家里的顶梁柱折断,小北家在堡子里就算坍塌了。娘带着小北一路往南,要去他爹说的南方讨生活。
母子二人沿途乞讨,荡了三年,仍旧没有走到小北他爹说的暖和地方。冬天来时,虽说不常下雪,但湿冷的北风还是能吹进骨头缝,让人身冷心寒。三年过后,小北长高了不少,母子二人的境遇却没有任何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小北在乞讨不到吃食的时候,他会下手抢,抢到手就跑,启动速度与加速度之快,几乎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小北他娘起初不让小北抢,说人家给是情义,不给是情理。可好道理终抵不过饥肚子,天长日久,小北他娘也就默许了小北的明夺暗抢。
走到赣州的时候,小北的娘病倒了,倒下就没再起来,也再没张嘴说过话。小北在赣江北侧找到一处背静地,折几根竹子架起两领破席子搭了一个简易窝棚,把弥留之际的娘放在窝棚里。安顿好娘之后,小北则去了县城,想讨一碗他娘最爱吃的米粉。多数时候,小北讨要不到米粉。每每此时,闵记米粉摊的阿昭姑娘就会偷偷送给他一碗。阿昭年龄跟小北相仿,也是个流浪儿。阿昭扎一条细细且泛黄的马尾辫,身子骨单薄瘦弱,像一根刚刚冒出土的细毛笋。闵记米粉摊的老闵想雇用一个不花钱的伙计,就相中了沿街乞讨的阿昭。阿昭风卷枯草般的身材,让老闵觉得这女孩儿做衣裳省布吃饭省粮食。等到正式收下阿昭做伙计后,老闵当天就后悔了,阿昭吃下三碗米粉,还眼巴巴瞅着汤锅。老闵终是没有赶阿昭走,他老婆死后已经鳏居三年,明媒正娶没有那份财力,老闵盘算等着阿昭长几岁就把生米煮成熟饭。眼下阿昭正是长身体的年岁,就算是多吃几碗米粉,身子也是给他老闵养的。厘清这些得失,老闵暂且咬着牙忍了下来。
阿昭第一次把汤锅里捞出来的半碗米粉送给小北时,后脑勺就被老闵扇了一巴掌。从那以后,阿昭就把打烊前捞出的米粉置于显眼处,让心领神会的小北来“抢”。冬至那天生意不好,一天卖了不到三十碗米粉。傍晚掌灯时分,老闵撩起辨不清颜色的围裙,擦了擦粗糙如枯树枝的双手,对阿昭吼道:“收摊子。”
阿昭应了一声,拿起竹编笊篱,在汤锅里快速捞着米粉。汤锅里只剩下零碎的米粉儿,阿昭接连捞了十几笊篱,才够半碗。阿昭用眼睛余光扫了一眼老闵,看到他正低头装水烟斗,便赶紧往半碗米粉里添加佐料。同时,阿昭抬头望向城墙根,那里蹲着脏兮兮的小北,手里拎着一个瓦罐。阿昭合上装佐料的竹筒,又扫了一眼老闵,这才对着城墙根下的小北轻轻点一下头。小北悄悄起身,拎着瓦罐磨磨蹭蹭地凑近米粉摊儿,随后一个箭步抢过来,抓起半碗米粉倒进瓦罐,转身便跑。老闵扔下手里的竹筒烟,冲着小北背影骂道:“噎死你个小北佬!”
小北跑得极快,快到几乎没听到“小北佬”三个字。小北沿着城墙一直跑到赣江边,在河岸背静处找到他娘,把瓦罐放在破席上,伸手扶他娘的时候,才发现娘的身子已经僵了。小北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捧着娘的头号啕大哭起来。哭一阵子,抽泣一会儿,哭哭停停到了半夜时分。月亮照在赣江上,像是一碗雪白的米粉凝入水中。恍惚间,小北看到一个单薄的身影搅乱赣江中的米粉,阿昭怯生生地站在眼前。
小北问阿昭:“你来做什么?”
阿昭理了理散乱稀疏的头发,咽了一口唾沫,这才说道:“刚才……就在刚才,老闵光溜着身子……进了、进了我的屋,问我为什么把米粉给你,还问我……是不是跟你相好了。”
小北问道:“你咋回他的?”
阿昭说:“我没回,吓得我赶紧翻窗户跑出来……找你。”
小北说:“找我……做啥,我也养不了你吃饭。”
阿昭说:“找你……不做啥,有饭就吃,没饭就不吃。”
小北说:“吃饭是天底下顶顶重要的事,没饭就得找饭吃,实在没辙就得抢。”
阿昭两手拧着蓝染布衫,在窝棚跟前坐下,说道:“抢也行,只是别让人逮着。”
小北没有说话,阿昭又说道:“别人也逮不着你,你是我见过的跑得最快的娃儿。”
小北也跟着阿昭坐下,说道:“有一天,我梦见赣江变成金黄色,江里的水变成小米粥,江心是稀的,江边是稠的,我娘喊我别往里走,就喝边上的稠粥。”
阿昭大概是被小北做的梦感染了,她说道:“你们北方人喜欢喝小米粥,最好江心是稠粥,江边是米粉。”
两个孩子坐在赣江边上,守着小北死去的娘,天一句地一句说着话,一直说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小北跪在窝棚前,朝着他娘磕了三个头。阿昭犹豫了一下,也跟着小北跪下来磕了三个头。接着,小北找来一根竹竿,把脚下的沙子捣松,再用双手把沙子扒拉出来。阿昭很快明白小北的用意,她蹲下来帮着小北一起挖沙子。江边全都是淤沙,沙质又很松软,两个人很快挖出一个大沙坑。小北把窝棚上的两领破席子扯下来,把他娘裹在席子里面,然后埋进赣江边的沙坑里。
阿昭掸了掸蓝染布衫上的沙土,问小北:“你要去哪儿?”
小北说:“我要去南方,南方暖和。”
阿昭说:“我也要去南方,我跟你搭伴一块走。”
小北点点头,抹去脸上的泪水,笑着对阿昭说:“咱们走吧。”
两个孩子沿着赣江江岸,一前一后往南去了。
阿昭问小北:“你叫什么名字?”
小北愣了一下,说道:“我没有名字,我娘一直管我叫孩儿孩儿孩儿。”
刹那间,阿昭觉得小北佬比自己还可怜,因为自己有名字,小北佬连名字都没有。
阿昭又问小北:“你老家是哪里?”
小北说:“好像是西北,我娘说我们原先住的地方叫童家堡子。”
阿昭说:“那你应该姓童。”
小北说:“我不姓童,我娘说童家堡子都姓童,只有我们一家外姓人,所以我爹死后,我们在童家堡子待不下去才出来的。”
阿昭一直跟在小北屁股后面一竿子远的地方,小北跟他说话的时候时不时要回头。小北停下来,冲着阿昭招招手,示意她过来一起走。
阿昭脸上露出笑意。她走到小北跟前,说道:“你是北方人,那我以后管你叫小北吧。”
小北愣了愣神,说道:“行吧,小北就小北。”
小北追到第二个路口时,已经能看清楚劫匪左侧耳朵上的黑色胎记。劫匪整只耳朵连同耳冠上面都是黑色的,这劫匪也真是黑到头顶了。接下来,小北只换了两口气,便把手搭到了印有“中华足球队”字样的皮包上。黑耳朵劫匪转过头来,小北稍松了口气,原来劫匪的面色与常人无异,就只有左耳朵的背面是黑色的。小北抓住皮包,用力拉扯一把,把正在奔跑的黑耳朵拽得一个趔趄。黑耳朵怒目圆睁,挥拳砸向小北。小北缩脖撤身,“嘭”的一声撞翻身后一辆木制推车,竟然听见女孩子的惊呼声。小北扭头一看,一个女孩瘫坐在手推车旁边,一双丹凤眼里满是惊恐,身边全是从推车里滚落出来的食盒,白切鸡、叉烧肉、煲仔饭、猪笼饼、水晶包、干炒牛河……撒了半条街。就在小北愣神时,黑耳朵又一记重拳扫过来。小北侧转过脸,再次躲过黑耳朵的拳头,就着对方发力的方向顺势推了一把,黑耳朵一时失了重心,扑倒在地的瞬间松开了抓皮包的手。小北拎着皮包撒腿跑了两步,旋即又折回,将散落在地上的叉烧肉、水晶包和猪笼饼胡乱抓起来,塞进怀里。丹凤眼姑娘愣愣地瞅着小北,却没有阻拦他往怀里塞那些食物。此刻,黑耳朵已经站起身来。小北顾不上再去拿其他东西,他直起腰身,抬起腿来踢中黑耳朵的肚子。黑耳朵惨叫一声,摔倒在一盒肠粉上,把一个食盒压散了架。待黑耳朵叫骂着爬起身来时,小北已经消失在路口。
小北一手拎着皮包,一手护着怀里的食物,脚底下竟是不慢丝毫。他在一条破败的巷子里七拐八拐,转眼奔出巷子,跑进一片香蕉林。香蕉林里有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两间木板和沥青纸搭成的窝棚,小北一脚踢开一块破门板,低头钻了进去。窝棚里光线昏暗,小北站在里面缓了片刻,立即有三五个小乞丐围拢上来,他们全都是嗅觉灵敏的主儿,早已闻见食物的味道。小北把怀里的东西掏出来,分给小乞丐们,脚却不停歇地走到窝棚最里面。这里有一块垫高的木板,木板上躺着一个面容憔悴且消瘦的女孩,闭着眼睛,微张着小嘴巴。小北在女孩旁边蹲下身来,从怀里掏出两个水晶包,轻声地说:“阿昭,阿昭,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你最喜欢吃的水晶包。”
阿昭睁开眼睛,眼神散乱游离,随即咳嗽起来,一声比一声剧烈。小北赶紧把阿昭扶着坐起身来,以便让她顺畅呼吸。在阿昭颤抖粗粝的咳嗽声中,小北示意一个小乞丐端来一杯水,放在阿昭睡觉的木板上。水杯是一只摔断把手的陶瓷杯,杯身上印有“MUG”英文字样。随着阿昭的咳嗽,陶瓷杯里的水也跟着有节奏地震动着。在阿昭咳完的间隙,小北喂她喝了一口水,接着把两只水晶包捧到阿昭面前。阿昭抬手接过两只水晶包,急火火地咬了一口,憔悴的脸颊上绽出难得一见的笑意。阿昭打心眼里喜欢小北,小北虽说有点野,能偷能抢也能打,但他心地善良。小北从来不吃独食,每回抢来的食物都会分给小乞丐们。他对这些不沾亲不带故的乞丐们都这么好,将来对待自己肯定会更好。事实上也是如此,小北每回抢到水晶包都会留给阿昭。小北对阿昭说过,他将来一定会抢一个有钱的大佬,给阿昭买一栋房子。小北还说,等到有了房子就娶阿昭当老婆,结婚的时候会把乞丐兄弟们全都请去喝喜酒。
刚刚把两个水晶包吃完,阿昭再次咳嗽起来,仍是一声比一声急促,惨烈得似乎要把肺脏咳碎了吐出来一样。小北似乎听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来对还在咳嗽的阿昭说道:“你等着,我马上就有钱了,拿到钱就带你去看医生。”
小北说完就要往外走,一抬头却看见窝棚里又多了一个女孩,正是刚才在街头被他撞倒的丹凤眼女孩。
不等丹凤眼张嘴,小北便对她说道:“你也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拿钱回来赔你便当。”
三
前往莲香楼吃早茶的路上,余伯庸顺道去了一趟警察局报案,说自己刚才遭遇劫匪抢劫,被抢走两千块钱现大洋。值班警察如实做了记录,让余伯庸在报案记录上签字。随后,值班警察告诉他,案子算是登记了,至于能不能派出人手来破案,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余伯庸心里明白,值班警察要敲诈他。但值班警察不知道的是,余伯庸巴不得破不了案。但是余伯庸脸上不露一丝欣喜,反而拍案而起,指着值班警察的鼻尖骂道:“这个操蛋的世道越来越糟糕,不是刁民太多,而是这个体制太腐败,充斥着像你一样的蛀虫,刁民上行下效有样学样儿,怎么会好?这个钱不是我的,是民国国库拨款,案子爱破不破,耽误中华足球队去菲律宾比赛,是国家之耻,而非我余伯庸之辱!”
在警察局撒完气之后,余伯庸款步上了莲香楼,麻溜地点了一壶铁观音、一份豆豉蒸凤爪、一份酱汁金钱肚、一屉水晶虾饺、一笼鲜虾红米肠,自顾自地大吃起来。想起这个季节的东北老家,只有酸菜和玉米面馍可以吃,余伯庸肥硕的脸颊上泛起油亮的惬意。美食可以冲淡一切烦恼,即便是在一夜输掉五百块现大洋的早晨。
天上飘起只有南粤冬季才有的牛毛细雨,屏住气息会听见天地间有一片细微的“沙沙”声。这样的声音不仅润嗓子润肺,还能滋润每一个飘荡的游魂。南粤遍地都是香蕉树、芭蕉树、龟背竹等大叶子植物,确实极难体会到北方细雨“润物细无声”的情调。因此,每逢下雨,余伯庸都想找一处高地,以免听见“噼噼啪啪”雨打芭蕉的吵闹声。莲香楼也算是雨中一个好去处,吃饱喝足后,余伯庸呷着浓茶瞅着窗外的细雨愣神。好在南粤的雨不扯不恋,来得急去得也快,一顿早茶的工夫雨便歇了。站在莲香楼的门外,余伯庸伸手招来一辆黄包车。车夫是个熟脸儿,问道是不是去慈慧庵。
余伯庸坐在车上剔着黄板牙,对着车夫骂道:“丢你老母,你才去慈慧庵,我去师范学堂。”
广州师范学堂足球场西侧有一排欧式建筑的二层楼房,一层有两间健身房,会议室、食堂、库房、办公室、会客室各一间。二楼是中华足球队的宿舍,漂亮的罗马柱后面,挂满球员们晾晒的运动服,有的还在滴水。球队的队医廖月英正在往一只保温桶里倒水,她在为球员们配比放了中药的饮品,以保障球员们尽快恢复体能。廖月英还是队长李惠堂的女朋友,出身广州一个名医辈出的中医世家,成年后留学法国研读西医。归国后,在同学举办的一次生日宴会上认识了李惠堂,一年之后两个人便订下婚约。
上午再次飘起细雨,中华足球队的队员们都在健身房练力量。司职左前锋的陈镇和正在跟左后卫谭江柏较劲比卧推,同样九十公斤的杠铃,两个人躺卧在木条凳上,在全体队员的监督下,以同样的频率卧推到十三次。第十四次的时候,谭江柏的两条胳膊开始微微颤抖,眼帘额头上的青筋也凸出皮肤。陈镇和的频率却依旧不变,配合着均匀的呼吸,当推举第十九次的时候已经领先谭江柏一次。谭江柏颤巍巍地推举第二十一次,举到一半便放弃了,眼看着杠铃杆砸向自己的胸口,两侧负责保护的队友赶紧接住杠铃头,放到卧推架上。谭江柏依旧躺卧在橡木条凳上,把头扭向一侧,看着陈镇和正在举起第二十五次杠铃。
队长李惠堂示意在陈镇和两侧保护的队友接过杠铃,随即笑着宣布:“比赛临近,不要受伤,本队九十公斤卧推纪录是二十五次,谭江柏挑战失败。”
谭江柏笑着坐起身来,并从短裤口袋里掏出一块钱拍在陈镇和的大腿上,大腿上的汗水粘住一块现大洋。
陈镇和抬起大腿,拿起这一块钱来,高声笑道:“今晚的夜宵,我请客!”
谭江柏对着陈镇和胸口击了一拳:“球队第一大力王了不起啊。”
陈镇和笑着对谭江柏说道:“去年这个时候你是第一,人生就是这么难以估摸。”
一众队友兴高采烈地叫好,喝彩声还没落下,余伯庸踱了进来,哭丧着脸对李惠堂诉说两千块钱比赛经费遭遇“抢劫”一事。现场气氛立时凝固,因为这两千块钱费尽周折才得以批准。民国体育部门原则上只想支持个人体育项目,像足球、篮球这类集体项目参赛人数多,拿奖牌也只能拿一块,他们算的是经济账,因此在比赛经费额度上卡得极严。此刻,重新申请参赛经费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中华足球队原定三天后就要启程,奔赴菲律宾参加远东运动会。李惠堂眉头紧锁,目光如炬地盯着余伯庸,他对眼前这个吃喝嫖赌俱全的肥仔历来不信任,若不是看到其在商业运营方面的超人长处,早就将其拒之门外了。
李惠堂深吸一口气,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对着余伯庸问道:“你还有其他补救措施吗?”
余伯庸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说道:“办法倒是还有,可就得劳您大驾,跑一趟广州商会,凭借您的声誉和威望,募捐个三五千块钱应该不会是难事儿。”
李惠堂沉吟半晌:“这种事儿说起来让人着实难以相信,怎么会有如此巧合?”
余伯庸嘟囔道:“这寸劲儿可不就让我倒霉的赶上了嘛。”
李惠堂说:“中华足球队是国家的球队,可咱们球队只要有事儿就去人家商会求援,长此以往,人家还以为我李惠堂是去打秋风的,唉……”
余伯庸说:“这个您大可不必放在心上,我有个办法,能让商会自己找上门来,以解咱们燃眉之急。”
|
|